塞纳河之巴黎
幸运的塞纳河呵, 从来无忧无虑,
日日夜夜, 平静地流淌,
它涌出源泉, 沿着河岸漫步,
穿着绿色的美裙, 拥着金色的阳光,
冷峻矗立的巴黎圣母院呵, 也对它嫉妒不己,
经过神秘地带, 那神秘的巴黎,
它流向阿佛尔, 终于隐逝大海。
——–PREVERT 的《塞纳河之歌》
启航
曾几何时, 巴黎——一个遥远的国度。就在今朝, 巴黎——一个圆梦的地方。那个秋天, 有些落寞有些惆怅的我选择了巴黎, 也由此开启了一扇门, 一扇通往欧陆文明和逃离过往尘缘的门。
10 小时的飞行, 飞机顺畅地航行在云间。阳光将机身下的云朵晕做为粉紫, 温和的金色急迫地越过云隙钻来, 万千的金针灼痛了我的眼。关上旋窗, 和身边老人随意地聊, 巴黎就近在咫尺了。
独自, 卸下行囊。由此, 我和巴黎开始了秋凉的对话。依旧独自去了艾菲尔铁塔, 登上塔顶, 已凉的秋风在高空(274 米)将我的长发吹散,我禁不住瑟瑟地抖。触目的是城市中蜿蜒的塞纳河, 河道两侧风格各异的著名建筑群。那是拿破仑墓、巴士底狱、奥塞博物馆、巴黎圣母院……还有西奈半岛,一路望去, 另有一座座不同的桥梁横跨在两岸, 将那些个著名的建筑物连在一起, 也将整个法兰西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暮色苍茫了, 在天边。上来个法国男子, 头戴鸭舌帽。也是瑟瑟的, 佝偻着身子, 将手揣在裤兜里。和我一样瞅着黄昏的巴黎, 良久。瞥了他一眼,步下铁塔。据说:夜游塞纳河是巴黎的奇景。只是每天 20 : 00 才开游船。于是, 我孑然徜徉在河边。那里有高大的橡树林,又或是其他的树种。椭圆的绿叶飘在林梢, 也有一些泛了黄, 翻转而落:林中有长椅, 却极少的人。我单挽着双肩包, 手插在袋里,慢慢地踱在静谧的林蹊:褐色的枯叶飞转, 或疾或缓。落在我肩头, 拂去了:落在脚下, “吱嘎”地响。此刻, 不敢相信,我的已然从南半球的那方热土来到了凉意如是的北半球。一丛蒲公英开着瑟缩的小黄花, 一个结成了的蒲公英摇曳地, 被晚风拔起一蓬,漫天飞去了。这熟悉的植物告诉我:真的是北半球了。
随便买了点吃的, 终于挨到 20 : 00 。 8 个欧元的票, 上了船, 船分两层, 各有很多露天的椅子。存着登高远望的心理,我疾步上了第 2 层。 2 层中央有个小驾驶舱, 舱外一个红白相间的救生圈和缆绳。舱顶一盏探灯照向前方, 我坐在灯后的暗影里。回望船后,曾经登临的艾菲尔铁塔被橘色闪烁的灯火勾勒出美妙的身形。我以为:较之白天, 它要更美。船侧的舷下也有灯将光影投在水面,使冷风的河面多了份暖意。很快, 橘红色的座椅上就坐满了人。旅游淡季对巴黎来说, 是毫无意义的。“呜……”地一声汽笛长鸣, 游船开动了。登时,船上的人们兴奋起来, 嗷嗷地欢叫着。我猛然发现,人在开怀或者忧伤的时候是没有语言差异的。这些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雀跃起来发出的声息是如此相似。渐渐地欢呼的人们安静下来。舱顶的喇叭里也传来优美动听的配乐解说, 将塞纳河两岸的建筑娓娓道来, 它的历史, 它的今天。巴黎, 这座由塞纳河左岸发展起来的都市, 这里的一切无一不著名,无一不经典。同样的语意经由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这些不同语言的诠释, 虽不甚懂, 但听来都是那么柔和、悦耳,这温情的解说, 波光潋滟的河水和我们所乘舟楫的轻摇都让我恍然如梦。
船平稳优雅地航行着,两舷的灯火更加丰富起来, 河水妩媚地闪着眼眸, 好似豆蔻女儿般欲语还羞。宽阔的水面上, 有其它的游船错舷回转,我船的游客兴奋地朝他们挥手致意, 对船也热情地回应着, 在这自然水美之中似乎人与人不再有距离。飕飕的冷风里, 我竖起牛仔短装的领子,尽管里面穿了羊毛衫, 可还是难于抵挡夜的风寒。将黑色的披肩箍紧双肩抱在胸前, 只是胸腔里那颗砰然跳动的心和不停地激动叫喊,才能让我抵御寒冷。右舷划过一条游船, 船上有敞亮的船舱, 里面疏落有致地摆了桌椅。一些衣着鲜亮的们坐在里面,里面还有乐队正奏响优美的小夜曲。那音乐具体是什么, 我听不真切, 但从那温暖柔软的光线, 男女脸上隐约的笑魇, 雪白的桌布,戴着领结的侍者和他们小心翼翼的行走, 可以断定这是一艘豪华游轮。此刻, 看着这一船行走着的舒适, 终于明了花都巴黎成为名媛贵妇的天堂的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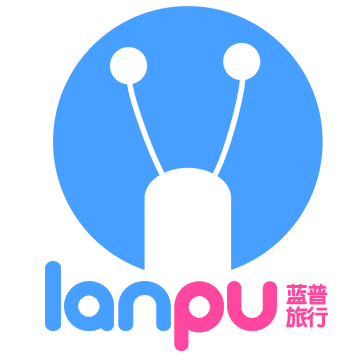
评论